《又见奈良》剧情介绍
电影讲述了一段跨越60年的异国无血缘母女情。年近八十的老奶奶陈慧明(吴彦姝 饰)孤身奔赴奈良,寻找失去联系的养女陈丽华。在遗孤二代小泽(英泽 饰)和退休警察一雄(國村隼 饰)的帮助下,找到了许多接触过、帮助过丽华的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陈慧明如同亲历丽华到达日本之后的人生,她与小泽、一雄之间的关系,也在这段旅程中更加贴近了。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新网球王子冰帝vs立海未来之战死亡博士密使魔发精灵的假期暗战风云承诺勒克瑙之花如果能成为恋人IceFall猫屎妈妈蝶变计划女子监狱第七季东陵盗宝之徐公馆诡事逃学神探时光之轮第二季脱离雪宝的冰雪大冒险纵横千里之一发千钧花样中年我要嫁印侨神探·人兽·机关枪终极游侠LoveLive!虹咲学园学园偶像同好会四格漫第二季伯尔尼的奇迹双世宠妃Ⅲ出云战记台风商社完美有多美1941之春隋唐英雄4
《又见奈良》长篇影评
1 ) 憋了一口气,泪湿一双眼
太好看了,但太难受了。
低气压,空前的低气压,久违的低气压。
尽管字幕已经出来了,尽管灯光已经亮了,尽管结尾的音乐都挺了,可与我同场的观众没有一个站起来走的,我们全在等一个彩蛋,等一个转折,也许下个路口老人就能与女儿相遇。
然而……导演若不是爱的深沉,就是没有心,这结尾是如此突然,又在情理之中,视角清冷的好似旁观的上帝,又像无声的控诉。
当然,除了这些,我看完还有一个念头冒出来,一个团队,一条线索,寻找一个答案中国人,在日本,有笑点,有悬疑。
跟最近一个电影好像啊!
噢,对了,他们还都关于日本战败后日本遗孤回国后的处境。
你猜怎么着,奈良完胜。
2 ) 《又见奈良》首映见面会场记录
鹏飞导演致谢(省)吴彦姝致谢:我到奈良没有找到我的女儿,但是我在上海找到了你们。
你们是我们这个片子的第一批观众,上海观众是我们的福气,上海是我们的福地,谢谢大家。
英泽致谢(省)主持人,观众提问环节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导演,最初创作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而且我们看到这是贾樟柯导演以及河濑直美导演作为监制,而且题字也是河濑直美导演,给到我们很多帮助,可以聊一下吗?
鹏飞导演:影片的开始实际上是我上一部影片《米花之味》参加奈良国际电影节,也就是河濑直美的电影节,那就有一个机缘和她合作下来监制这部影片。
因为中日合拍,所以河濑直美也找到了她的好朋友贾樟柯导演,那就一拍即合开始合作。
鹏飞导演主持人: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是你决定去做的吗?
鹏飞导演:对对对,当我知道我要拍一个中日合拍的影片的时候我在想,因为中日之间有很多的历史,很伤痛的历史。
所以我决定我要拍一个这种大背景的题材,我一开始就决定拍一个可以说是反战的题材,展现人性的光辉。
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查了很多资料,后来就决定拍遗孤与养母的故事。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吴彦妹老师《又见奈良》的故事哪里最打动你?
吴彦姝:我觉得就是寻找。
整个寻找的这个过程体现了一种友爱,体现了母亲的大爱,体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的一种友爱。
所以我觉得这个寻找是建立在爱的这条线路上的一个表现。
主持人:我们再来问一下英泽,这次是与吴彦姝与日本演员国村隼两位老师合作的感受如何?
跟两位有学习到什么吗?
英泽:真的学习到很多,很感恩能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和吴老师有很多的对手戏,有她在的时候我感觉入戏什么的都非常简单,她就像一位奶奶在我面前,然后又有一些亲切与可爱,我也很感谢吴老师对我的一些鼓励,包括国村隼老师对我的日语很大的帮助也有很大的鼓励。
观众问答时间观众A:我没有想问问题只是想发表一下感想……我觉得这部电影做的最好是它的声音,它对于声音的运用特别好,无论是寺庙大钟敲打的声音,还是唱戏的戏腔,与最后邓丽君的《good bye my love》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异乡的情结,但我会很容易代入到故事里面去共情,去流泪。
谢谢导演……鹏飞导演:谢谢你。
实际上你刚提的寺庙撞钟与邓丽君的歌曲,其实它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融入。
一开始我去看景的时候,我日本的同事带我去这个地方看了很多的景,很多都是神社,我去到神社觉得很陌生,很不自在。
有一天去了当地的寺庙,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很熟悉,有回家的感觉。
包括邓丽君的歌曲也是,她在中国与日本都很红,唱同样的旋律但用两种歌词,带给我一种熟悉感吧,我相信也是丽华与这些遗孤在他乡听到的歌曲。
观众B:感谢导演呈现给我们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你的前作《米花之味》还有与蔡明亮导演合作的《郊游》,我一直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想问的是你创作时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巧思,我想知道这些巧思的灵感来源在哪?
比如两位老年人在互换照片的肢体动作,包括无实物的唱戏,这是一种比较幽默的呈现方式,不会太过于沉重或者刻意,我想知道导演创作的方式与灵感的来源。
鹏飞导演:其实这是一个很悲伤的题材,如果把它拍的很煽情也好,很悲痛也好,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
但如果拍轻盈一些,有一点生活中的幽默,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让观众观看时没有太大的负担,但是能体会到背后的沉重。
关于创作上,我都是根据亲身体验来的,我在19年全年都在日本待着。
在奈良与我的同事真的去寻找一些遗孤,你说到那个唱戏这段,其实我们是在深山里找到了一对遗孤,和他们聊着聊着就拿出一把二胡来,一边拉一边唱,拉的很难听,我都不知道唱的哪出戏,但是他拉的满头大汗,眼睛里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
所以我想说这些遗孤虽然生活在日本但是接受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以这种方式呈现会把他们的命运感代出来,在日本生活的遗孤他们的生活条件其实并不好,没有太多乐器的方式来进行,用唱腔的方式来回忆中国,而奶奶与老警察的戏是即兴发挥的。
观众C:我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我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有趣的联系。
比如永赖正敏在河濑直美导演的作品《光》里饰演一位盲人,在这部电影里是一位聋哑人。
包括吴彦姝老师之前在《相爱相亲》里也是一位思念的人,思念逝去的人。
我想问一下导演这些选角,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一下如何选角与他们之前的作品有没有联系。
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村隼老师与英泽在车内的对话被电话打断了,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没说的东西被表达出来?
鹏飞导演:选角方面我倒是没有想到他们之前的电影,只不过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与国村隼老师的故事,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河濑老师就问我说日本老警察角色我可以帮忙找哪一位角色合作,她给出了几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三浦友和,第二个是演《深夜食堂》的小林薰。
当时我就掏出手机来说我想找他(国村隼),因为我觉得三浦友和先生对我来说太正了,这样一个正派气质去演有点凶的不太合适,一个很正的人去做一件好事可能没有国村隼老师这样打动人,有意思,有反差的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是车里的一句话是问小泽为什么没有回中国,这样就能找到亲戚。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小泽这一角色包括这些二代三代遗孤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在这边不习惯,但我为了赚钱也好生活也好等等……他们有一些苦衷,难以启齿,所以我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也是想告诉大家战争带来的伤痛并不是说在当代就能完结的,它会延续到很多代之后。
观众D与主持人:导演是如何让你的剧本更扎实,有没有真实的还原当时真实的一个情况。
鹏飞导演:实际上我们有两对演员是真实的遗孤后代,一个是飞机场的老先生,还有一个唱戏的女士,但他们是二代遗孤,他们饰演的是他们的父辈,所以大家也是能看到真实的遗孤的状况与状态。
我在写剧本之前把所有关于中国养母的书都看了一遍,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书采访每一个养母,问每一个养母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她们就说我们的愿望是去日本看孩子,至少看看孩子的故乡是什么样子,但实际上很少很少的养父母能去到日本完成这件事,所以我希望用电影来完成他们一个梦想。
3 ) 中国人永远臣服于“团圆”和“回家”
第3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有福电影”巡展《又见奈良》。
感觉对我来说也算某种意义的“公路片”,很平静的剧情片,看的人心真的会静下来。
中国人永远臣服于“团圆”和“回家”,到最后10min的“明”让我泪目,隔壁也在偷偷抹眼泪。
如果不是电影节展映有免费票,我平常不太会主动看这类型电影。
绝对不是说这种类型不好,其实很多得奖的影片类型都是剧情片,只是个人喜好不同罢了,我平常有时间喜欢看直给的打打杀杀爆米花,感觉特别解压、畅快
4 ) 必然的失落,温柔的凝视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养母寻找日本遗孤养女的电影。
1935年开始,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向中国东北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日本农业贫民,称之为“日本开拓团”。
日方战败撤离后,开拓团成员也四处流散,混乱过后,许多被抛弃的孩子被中国民众领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
片中的“女儿”陈丽华便是日本遗孤之一,被陈慧明奶奶领养,并在中日建交后选择回到日本。
影片便从陈慧明只身来到日本寻找养女开始的。
整个故事像一张缓缓铺开的画卷,并不刻意地设置巧合、急着要找到丽华的下落——它只是试图抚平观众急不可耐的心,向人展示如此复杂的人生。
陪同陈慧明寻找遗孤养女的,还有身为战后遗孤二代的小泽和留守老人一雄先生。
令人宽慰的是,他们都不是为了寻找丽华而设置的“工具人”,影片细心地刻画了他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困境。
小泽的父亲是陈慧明奶奶的朋友,也是日本战后遗孤之一,然而回日本后认亲受挫、最终选择留在了中国,小泽选择只身留在了奈良。
这个年轻女孩为了生存下来,做过导游、做过居酒屋服务员、也做过流水线工人......就算看着电视都要一边做手工活赚取着微薄的收入;客人问起她的口音,她强调自己就是日本人——生存,以及身份认同,是她的困境。
一雄先生是一名退休警察,妻子已经过世,唯一的女儿远嫁多年。
他每天在外游荡到很晚才肯回家,并且每晚回家的时候都要伸手摸一摸信箱,然而那儿始终空空如也——孤独,是他的困境。
他把对女儿的思念投射到小泽身上,于是同小泽和奶奶一同踏上了寻找丽华的道路。
他们去找丽华曾经频频更换的住址,去找她曾经的老板娘,去找她信上的朋友和画上的风景......得到的消息却并不乐观。
得知丽华可能已死的那个晚上,小泽发现用来拍了一路照片的相机里并没有胶卷,她哭着说:“都白照了。
”尚未知情的奶奶安慰她:“那些都留在我脑子里了。
”这里似乎有一个隐喻:大概是自从有了对死亡的考虑、并得出人生苦短的结论之后,人总是习惯从时间里截取、并留下点什么。
拍摄照片便是这样一个试图挽救记忆的过程。
可这归根结底是徒劳的,我们越是想挽救记忆,越是发现有更多东西流逝掉了,人面对时间的洪流无能为力。
同样,人要面对的洪流不只是时间,还有政治、命运等等,许多情况下,人只能被裹挟着前行。
这片子里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如此。
那么丽华的下落究竟如何?
通过影片末尾的一场祭祀礼,我们或许可以拼凑出一个由于语言不通而生活困难、四处流离,难以融入社会,最终孤独地死在出租屋里的丽华。
丽华已死,那么其他人呢?
他们的困境在影片的最后有得到解决吗?
似乎也并没有。
因为真实的人生即是如此,困境是永恒的。
只是在这种必然的失落之中,影片没有全然放弃对人生的那种温情脉脉的凝视——奶奶与肉店店员语言不通,互相“咩”呀“哞”呀地交流着;奶奶体谅小泽生存的辛苦,所以一有时间从包包里掏出材料帮她做手工活;奶奶同一雄先生沉默着互相欣赏他们与家人的合影;聋哑人管理员为他们敲响钟声;影评的最后三人步行的长镜头以及缓缓响起的邓丽君的歌声......这些温柔的凝视,给必然失落的现实涂上了一层治愈色彩。
再怎么注定失落的人生,总也因为这些温柔而值得一过。
5 ) 孤独的人啊
在电影院安安静静看了《又见奈良》。
星期五晚上6:40的场次,观影人数不到十人。
或许是之前期待太高了,观影时及观影后似乎都有一些失望。
吴彦姝和国村隼的演技没得说。
尤其是他们两个在乡村里寻找管理员时,两个人语言不通有些相对无言,就拿出照片给彼此看。
之后又无话可说,吴彦姝饰演的奶奶就拿出牙签教国村隼饰演的吉泽做小旗子。
100个才50日元,折合人民币4元。
她和英泽饰演的小泽有一次在等公交车时也在做小旗子。
这部电影中无处不在的都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拮据朴实无聊琐碎和善意。
电影设定的时间是2005年。
1995年时,战争遗孤陈丽华回到日本寻找她的家人。
她给在中国的养母写信寄照片,告诉她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
但是,四五年前,她音讯全无。
奶奶放心不下,她只身来日本寻找她的养女陈丽华。
奶奶随身携带的包里妥帖地保存着陈丽华写给她的信。
陈丽华的字十分娟秀。
小泽和奶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大海捞针般寻找陈丽华。
由于他们不知道陈丽华的日文姓名,寻人几乎举步维艰。
先前,小泽在居酒屋打工时,客人吉泽说她很像自己的女儿。
他们再次相遇时,退休前是警察的吉泽在听了奶奶寻人的故事后,主动提出帮忙。
他联系了曾在警察局在人事科工作的前辈高仓。
通过高仓,他们找到了陈丽华曾经居住过的一处住所的房东。
房东开着饭馆,一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自己曾在中国旅行的经历,对臭豆腐念念不忘,但当小泽他们询问与陈丽华有关的事情时,房东立马变得警惕。
之后放松下来,告诉他们陈丽华不会说日语但曾在她店里炸豆腐甜甜圈,十分吃苦耐劳,后来,被误会偷了东西就离开了。
在找寻陈丽华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在日本过得一点也不好。
血缘鉴定失败,语言不通,穷苦潦倒。
但她却还是用画笔画下曾经见过的美景,并寄给养母。
后来,高仓来电说陈丽华日文名字叫做中村明子。
中村是曾经帮助她的律师的姓,而明则是取自养母的名字。
她孤独地死在了公寓中,很久之后才被发现。
小泽听到时泣不成声,而坐在车子后排的奶奶由于奔波了一天累得睡着了。
她听不懂也没有听到这个令人悲伤的结局。
但是,导演又增加了一段,他们听到另一种说法到别的村子去寻找嫁了人的陈丽华。
村子里正在举行仪式,歌舞喧嚣,奶奶拨开人群四处寻找却依旧无果。
他们三个人疲惫地走在路上,背景是邓丽君的歌曲グッドバイ・マイ・ラブ。
虽然导演没有言明,但我们都不难猜测,陈丽华的结局就如高仓所说。
不然,她又怎么会不给养母继续写信呢?
整部电影都有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孤独。
奈良很美但也很空,一个又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
没有什么快乐的人。
吉泽每天回家都要看信箱里有没有嫁到东京的女儿寄来的信。
但一封也没有收到。
所以,他把小泽当作自己的女儿。
小泽在日本叫做初美。
她在日本的亲戚仅有害怕他们认祖归宗会争夺财产的姑姑和堂哥。
所以,她的父母已经回中国了,她作为二代遗孤独自留在日本。
在居酒屋时,吉泽疑惑于她的口音问她是哪里人时。
她坚定地回答日本人。
这份坚定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暗示。
她和交往的男友分手,性格不合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男方家嫌弃她的出身。
她始终是个异乡人。
影片中,奶奶到肉铺买想买羊肉,但不懂怎么说就学羊叫,老板用动物的叫声回应她。
而且这个老板正是导演自己。
十分可爱。
小泽在直到陈丽华已经不在了,夜里忍不住啜泣。
奶奶问她为什么哭啊。
她说是因为相机没有卷胶卷,都「白照了」。
奶奶告诉她,没关系都留在心里。
我想奶奶对于结果其实已经有了预感。
但这趟奈良之旅对她来说也不全是感伤。
作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奶奶,哪怕前方道路多么曲折,她也会坚强地走下去。
6 ) 电影《又见奈良》:重重的爱,轻轻地说
不会日本语的老奶奶和肉店老板用动物的叫声来沟通;因为紧张,条件反射地说着俄语再见的老奶奶,再见的发音在日语里却是骂对方笨蛋的意思……这些充满喜剧元素的剧情都堆在了电影开头,差点让我忘记了这是一部说日本遗孤的沉重的反战题材的电影。
遗孤二代的小泽为人节俭、谨慎,在居酒屋打工时,曾是警察现在退休无所事事的大叔对她的口音有些好奇,于是问她是哪里人,她犹豫了半秒后坚定地称自己是日本人。
这个回答引起了我的好奇,毕竟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话,我自然会说“上海”,而不是回答“中国人”。
好在这个疑问在后面有了答案。
二战结束,在中国,那些被日本父母遗弃的孩子成了在当地长大的日本遗孤,陈丽华就是其中之一。
当陈丽华长大后知道自己是日本人时,1994年她选择回日本寻根。
重回日本生活的她一直和中国养母书信来往,直到有一天,查无音讯,年迈的中国养母老奶奶在2005年来到日本开始了寻找养女的故事。
电影也正是从老奶奶投奔于同样是已在日本重新生活的遗孤第二代女孩小泽的家中开始。
老奶奶、小泽,以及退休闲来无事的警察大叔成了寻亲三人组,当他们在奈良山区的遗孤一代的夫妇家中,看着两人用纯正北京味的发音,怀旧地唱着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段时,我不禁问自己,对他们来说,到底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
中国?
日本?
这一群在战争时代的惊涛骇浪下,被卷入时空缝隙的人,无处安放的故乡,无处找寻的归属感,犹如生活在时间的真空地带。
既不是……也不是……这种存在于时间河流中的两难境地,像极了另一部诉说空间真空地带的电影《幸福终点站》,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男主从巴黎乘坐飞机到伦敦,结果护照掉了,又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于是,他既不被允许进入英国,也无法走出机场返回法国,最终,他住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的1号航站楼长达18年。
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和无奈,仿佛是命运开的魔幻玩笑,让人心酸。
有人说,战争没有真正的胜者,被战争席卷的每一个时代下的小人物都无法逃脱它的创伤。
记得几年前给某节目选晚安故事时,挑了一篇二战时期,法国小男孩潜伏在酒馆智斗来看演出的德国军官的故事,男孩的突袭屡屡获胜,就在大家看得大呼过瘾、拍手叫好的时候,一位经历过抗战的报社老前辈打电话告知节目组,“这类故事尽量少播,尽管和平也是用战争换来的,但战争波及的不幸范围,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当时,我一直不解,难道为和平奋勇而战的弱者,他们的故事不值得称赞、播出吗?
如今,终于懂得老前辈的意思,因为,战争没有真正的胜者,每一个被卷入战争洪流的小人物,战争带来的创伤,他们都无一幸免,无论是遍体鳞伤抗战成功的胜者,还是节节败退仓皇逃走的败者,胜负只属于国与国,而伤痛却遍及这个时代的所有人。
1945年日本战败,那些被遗弃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很多都被中国家庭收养。
导演说,这是无法描述的人性的光辉。
更何况电影中年过八旬的老奶奶漂洋过海只为寻找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日本遗孤陈丽华。
那么,这些遗孤回到日本生活还好吗?
可以看见哪怕是第二代的小泽,仍在靠四处兼职打工谋生,和男友的恋情无奈终结,只因男友父母不同意找非日本人结婚,而那些一起寻找陈丽华的已经在日本驻扎生活的遗孤一代,一个在废弃的汽车回收场做着体力活,一个是回山里种田。
就连之前回日本的陈丽华在豆腐店打工时,由于店里少了东西,老板娘误以为是陈丽华偷的,于是将她赶走。
这似乎看来,他们的身份并没有被认同,甚至就连他们自己都是这么认为,就像汽车回收场的大叔从不接用日本语打来的电话,在大山里唱京剧反而亲切自在的遗孤夫妇,以及已经在日本生活的遗孤第二代小泽,在电影开头回答警察大叔时,犹豫过后假装坚定地回答自己是日本人的时候……一个因战争遗留下来的悬浮在空中的身份归属问题,同样深深地困扰着他们。
所有人都在找陈丽华,除了信件和照片,电影从头到尾她都没出现。
估计观众都猜到了,这位和母亲信件来往密切的人是不可能这么没良心地中断往来的,唯一能解释的是她已经死了。
也许,老奶奶在来日本前已料到了最不愿面对的结局,但又有哪个父母会放弃寻找孩子的最后一丝希望呢。
当他们听朋友说陈丽华嫁到隔壁村的时候,三人火急火燎地赶往山中,全村人都在参加祭祀,老奶奶迫切地挤过人群,一个个地确认,祭祀的舞台上鼓声阵阵,咚咚咚,嘭嘭嘭,那分明就是心跳的声音……最终,三人沿着长长的坡道走着,老奶奶擦了两次鼻子,三人沉默不语地在黑夜中往前走,长长的镜头,随着邓丽君的歌《再见,我的爱人》,没有尽头。
影片的最后又一次出现了陈丽华写给母亲的信:妈妈,我在这过得很好。
眼泪哗地流下,这是每个漂泊异乡的人,哪怕是搬离父母家开始新生活的人都会说的善意谎言。
重重的东西,你要轻轻地放。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晚安疯子
7 ) 就这样一直走着吧
业务看片会,体验极差,荧幕忽亮忽暗,差点没忍住想投诉,还以为没人发现,结果出来检票口听到工作人员说是片源问题?
看得眼睛要瞎了。
观影过程中厅里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玩手机,我坐第五排,眼前永远有2-5个满亮度手机屏幕晃我眼,大家就这么忙吗?
素质极差。
一直到开场半小时都有人陆续进场。
影片本身是可以的,克制却不隐忍,所有故事背景中的那些哀伤与痛苦,都很好地被生活中出现的小幽默与人消解。
即使他们在日本说着日语,电影的底色,依然是中国乃至东北人民独有的乐观。
陈奶奶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可爱了,也离不开吴彦姝老艺术家的出色演绎,希望以后还能多多看到她的作品。
英泽面对戏中一众演技派露了怯,直接导致这个主角毫无记忆点,甚至还不如导演客串的肉店老板讨喜。
导演吸取了中国电影与日本电影两者独有的气质和优点并且将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用一种看似简单处理却拥有极高完成度的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涵盖众多沉重母题的故事。
战争遗孀,历史洪流下的小人物,在战争结束后的七八十年后依然被阵痛波及,并影响一生。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当沟通交流失去媒介,是好还是坏?
导演非常巧妙地将一个老奶奶作为切入点,让我们一窥历史的一隅。
你可以说他拍小了,但不得不承认拍的很巧。
有几个片段拍的真好,聋哑人一段都很棒,两位老人的无声表演更是一绝,当语言因差异现状失去意义,属于不同国度的人之间的沟通却反而更加有趣。
结尾的处理在观影时看着有些突然与沉闷,甚至当时细想还觉得冗长与必然,但回过神来觉得还不错,就这样一直走着吧,所有人。
结尾其实有点没看懂,所以她到底死没死?
那个xx祭是干嘛的?
8 ) 《原来片名就说出了结局》
原来片名就说出了结局——Tracing Her Shadow,养母从头至尾都是循着养女的影子往前走,而养母这趟旅程的终点究竟在哪里呢?
没办法知道了,最后,伴随着日文的《再见爱人》响起,只知道他们在往前走而已。
旅程中拍摄的照片,打开相机后盖却发现没装胶卷,就仿佛是现实的隐喻,以实际而言,无法找寻到实体的人了,但是那句“照片都在我脑子里呢”又好像在告诉我们,关于养女更多的记忆镌刻在了养母的脑中——一个日本遗孤回到所谓的“祖国”后究竟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通过信传达来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组成了立体的人。
我不由地去想,对人而言,究竟是血缘与民族性在决定一个人还是文化在决定一个人呢?
一个完全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民族与文化冲突产生的自我认同感迷失是一个庞大的命题。
平常人大概永远只能作为旁观者而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挣扎。
但是我觉得我思考的不完全准确,其实电影更多的表达的是这类特定人群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所遭受到的排斥,以及展现部分人群的孤独——有很多类人的孤独。
2025.2.9标记二刷,上一次看是2021年3月20日,时隔快四年再看这部电影,时间过的快的。
9 ) 给倔强的奶奶
情节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都在内心暗自较量。
只说说奶奶这个角色吧,孤身一人踏上去奈良寻亲的她,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国度、投靠远房晚辈去寻找一个没有血缘、失联多年、却被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异国遗孤,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母亲也许只想在死前见一面孩子,出于舔犊情深的本能;失联的孩子却有多种可能性:生活的艰辛、身份认同上的疏离、生命的意外都有可能是造成失联的原因,说实话看的过程中我很怕失联多年的女儿突然出现,给出一个物是人非的交代,但又很期待奶奶可以在街角的酒屋或者是日料店,突然抬头就看到想要找寻的她,观影全程都是彼此纠结的。
全片凭借奶奶这位母亲寻亲的动力一路步履不停,循着养女遗留在人间一点点的蛛丝马迹走遍了奈良…一直走下去。
这片带给我的情绪很复杂,想起了我的奶奶。
上次她来到一千公里之外,我生活的城市,她很好奇地想把每个景点都走一遍,甚至走得都比我还健朗,在每个景点前留影,一点也不显疲惫。
在奶奶归乡时,她对着我说了一句,年纪大了这次回去就不出来了,哪儿也不去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每一眼都是最后一次,多看一眼算一眼。
奶奶回家后,我也只能一年见她一次,一次五天,算起来,我也算是她生活中的“失联人口”了,这辈子掐指算算,还能有几个五天啊。
再次想我奶奶,所以我想去理解片中奶奶的倔强,一旦放下,不知又何时,才能够“又见奈良”。
10 ) 《又见奈良》:再不拍,就没了
喜欢《又见奈良》,是因为它是那种“再不拍,就没了”的电影。
有那么一些电影会属于“再不拍就没了”的范畴,比如讲慰安妇群体的《二十二》,比如这部讲日本遗孤的《又见奈良》。
它们所记录的一群人,正在慢慢消失。
而电影本身的故事,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寻找这样的人。
所以,比起它其中的亲情、温暖,我更想来聊聊它的这种“再不拍,就没了”。
“日本遗孤”是典型的历史遗留群体,作为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撤离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是“被留下的”,其中那4000多名儿童,更是“战争孤儿”。
被中国家庭收养之后,他们在亲情意义上有了家,但在社会关系上,还是没有家。
按照今年是2021年来看,就算是当年留下来的婴儿,一代遗孤,也都已经70多岁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也是考虑到这部分因素,《又见奈良》才会把时间放在了2002年。
也正是这种时间上的后退,让我们看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演进。
那些战争带来的问题,依旧绵延在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人的身上。
《又见奈良》也在各个层面上都在呈现这种“历史意义上的消失”。
它最主线的剧情,就是说吴彦姝饰演的中国养母陈奶奶,去奈良寻找日本养女的故事。
养女丽华在回到日本试图寻找亲人后,突然失去了音讯,这本身就是一种“消失”。
寻找过程中,陈奶奶与二代遗孤小泽、退休警察一雄为伴,在这里影片借用了某种公路片范式,三人的寻找之旅,也是在一点点拼凑出丽华生活的原貌。
如果不是养母的寻找,丽华近乎可以被视为一个在社会和历史中隐去的人,中国人不接受她,日本人也把她看做中国人,她在只能在信里写,“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陈奶奶在寻找丽华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日本名字,也意味着丽华以及她背后的无数人,都被文化和国族剥夺了姓名。
这是《又见奈良》轻松温情语调背后的残酷。
片中的每个人身上也都存在着这种消失和隐去。
退休警察一雄每天都去看信箱,期待女儿来信,加入寻亲队伍给他带来存在感和有用感,这放到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日本社会背景下,是老龄群体在社会语境下的消失。
二代遗孤小泽在工厂里捡柿子,她的父母回到日本后又回去了中国。
她自己则选择留下来,但也并不被日本社会接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就是另一个丽华。
他们拜访的那些遗孤群体,或隐居在山中,靠卫星锅接受中文台,或在工厂唯唯诺诺勉力维持生活,如果不是这次寻找,他们也就在这种日常生活里隐去身影。
鹏飞导演是个很能用轻盈姿态去处理沉重议题的作者。
《地下香》用诗意去处理地下空间,《米花之味》讲留守儿童,却用很多笔墨去描写女儿身上让母亲束手无策的调皮。
《又见奈良》讲日本遗孤,却也会写陈奶奶在日本无法融入的境遇,比如她在没法说日语的情况下,学动物叫来买肉。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在“失语”情况下,依旧努力寻求沟通的表达。
为陈奶奶提供线索的聋哑人朋友,已经退出警察系统却努力动用资源的雄一,不用语言表达也能沟通交流的寻亲三人组,就是在以“沟通”突围“失语”的高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又见奈良》本身也就是一次试图突围“失语状态”的表达。
它是创作者代替历史的发声,是在风沙渐渐抹去历史痕迹时用影像对它的拓片,是一种对历史的挽留,而非私人的留恋。
这样的故事太容易滑向愤怒,创作者在面对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是需要节制的,而《又见奈良》难能可贵地在历史残酷里葆有了天真。
这种天真抱着负隅顽抗的姿态,但那可能就是普通人面对历史的姿态。
想看中文节目,就装卫星锅。
要吃饺子,就自己做。
女儿不见了,就去找。
这段历史要消逝了,那就把它拍出来。
++++本文首发于我的个人公众号“闵思嘉”,关注我撒。
传送门:https://mp.weixin.qq.com/s/Ysjhckb6PEadMAoRTqkp4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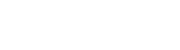





























这个系列一个套路,感觉新意不足
20180110保利剧院哈哈哈
最后的求婚很cool
This musical really sprinted, jumped hoops, and back flipped, so other musical adaptions of movies can wALK. Love this and love the og movie all the same 💗
现代音乐剧果然有好多现代元素。。但是歌并不动听。。差今年的tony 魔门经 远了
我的关注点在学长真的可以给学妹拨穗吗哈哈哈哈哈
還不錯看~
怎麼有兩個。。。
“Some giris fight hard, some face the trial. Some giris were just meant to smile.”
舞台剧版比电影版好看多了!学长好A!学长好帅!
还可以
美女
虽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看得超开心
从这部电影中我了解到,原来哈佛这么好进?
查漏补缺
三直接就换了主角,但故事还是不太适合律政俏佳人这个名字,有点感觉是小打小闹。
这是音乐剧!超棒的一个舞台剧被你们当作电影版打了低分!!!电影版出门左拐找同名,你们气死我了!!!!!
狗狗~
Fun!要是有字幕版就好了,等二刷!
毫无现实意义的爆米花电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分化。